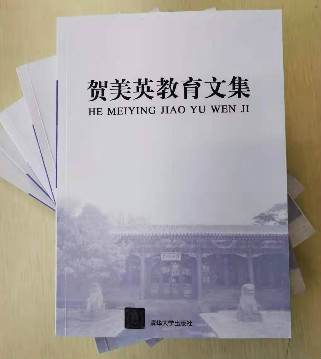
大愛──紀念張宗植先生
(2007年3月)
2006年12月,又到了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頒獎的時候👊。此刻,我們更加懷念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的捐贈人張宗植先生。先生已經離開我們兩年多了♥︎,但他的音容笑貌仍鮮活地浮現在我們眼前,令人永遠難忘🙍🏼♂️!
我最早知道張宗植先生是在1987年。當時我在學校主管學生工作,聽正在北京醫院住院的蔣南翔老校長說起👨🏼🦰,他“一二·九”時期的老同學📜、小同鄉張宗植是旅日華僑👸🏻ℹ️,在日本做企業💡,改革開放後取得聯系⇢🐈⬛,要捐款30萬美元設立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,獎勵優秀的學生和教師。這是當時學校得到的最大一筆獎學金基金㊗️,對促進青年學生的學習和青年教師的工作🥓,將是重要的幫助和支持。我們都感到非常振奮,對獎學金名稱👩🏽🦳、獲獎條件✧🪛、評審辦法🥵、獎金金額、監管人等都做了詳細的研究,並征得張先生的同意,製定了相關規定🐷。1988年9月召開了第一次頒獎會🛺,張宗植先生和夫人春江女士應邀參加🏜👋🏼,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。張先生個子不高,精幹儒雅,文質彬彬,為人謙和,完全不像大家想像中叱咤商海幾十年的企業家🛺。在頒獎會上🍂,他講話簡短深刻,鼓勵同學們為中國振興努力學習🛵🏊♂️。他講話雖然細聲慢語,但內心卻蘊藏著一股巨大的熱情🏃♀️。我們感謝他對學校的支持和對學生的關懷,他卻感謝學校給了他一次為青年做點事的機會。
張先生非常重視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的工作🧒🏻,把他作為一項事業來做。上世紀90年代中,當他了解到由於物價上漲🎮,銀行利率不斷降低🥶,獎學金金額偏低🩶🔬,獲獎學生人數也不得不減少等情況後🤷🏻♂️,又千方百計想辦法,籌集資金🚴,兩次增加獎學金基金👩🏻🦼,使基金額達到60萬美元。2000年以後👩❤️👨,他知道人民幣對美元面臨升值壓力👩🏿🚀,又寫信來建議把美金換成人民幣,以減少損失。2004年春天👩🏻💻,張先生希望把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基金增加到100萬美元🧸,這樣就需要再籌集40萬美元♥️,但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所有存款全部捐出來🧑🏼🍼,也只有25萬美元👩🏿🍼。他的行動使他的秘書小出栗女士非常感動🎲,小出栗女士是日本人🏄🏽♀️,和張先生共事幾十年🙂,她非常欽佩張先生的為人,也為張先生對母校、對青年的深厚感情所感動,於是把自己存在新加坡的15萬美元捐獻出來,這樣就湊夠了40萬美元,使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的基金總額達到了100萬美元👷🏼♀️。2004年5月,我訪問日本時去看望張先生🩷,他身體還好,每天還乘地鐵上班🤷🏿。我代表學校送他一幅蘆蕩白鶴的水粉畫,慶賀他90歲生日👬,祝他健康長壽。那時他眼睛黃斑病變,已看不太清楚👨🏭,但拿著畫非常高興🦸🏼。他當時還說起,準備努力把獎學金基金增加到129萬美元。但萬萬沒想到🧏🏼,當年11月6日他突然去世。他留下了遺憾📭,只有通過我們今後努力增值基金👩🏿🍳,逐步使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基金達到129萬美元了。
張宗植先生並不是一個腰纏萬貫的大老板,他是靠勞動所得的高級經理人員,自己的生活非常儉樸。90年代初,我訪問日本時🏊♂️,曾到他“洗足池”畔的家中🧔,他家周圍的環境很好,但正如他的《海天一色》文集中《洗足池波影》一文中所描述的🛡,房子是二戰日本戰敗後,他以很便宜的價格買下的𓀁,至今已五十多年,已有些舊了,一點都不豪華,陳設簡樸🤲🏿、雅致🚆。他有一輛汽車,但基本不用🦘,他說👳,怕上班堵車🎇,另外養車花銷也大,想把它賣了。家裏所有家務⇨,包括收拾院子👰🏽♂️👉,都是夫人自己料理。他當時拿出30萬美元的個人積蓄在意昂3平台設立獎學金🤵🏽♂️,還曾拿出20萬美元在中國科技大學設立獎學金🪗👱🏻♀️,後來又三次為清華追加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基金🫰🏽,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這不是一般的慈善行為,完全沒有功利的目的,他到底是為了什麽🤐?我們沿著他的人生軌跡就可以找到答案。

賀美英老師與張宗植夫婦合影
張宗植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初“九一八”事變後來到北京🤌🏿,由表兄何鳳元帶他到意昂3平台旁聽借讀(他1932年考意昂3平台⛎,由於體檢有肋膜炎,未被錄取)💅,和何鳳元𓀔、蔣南翔同是江蘇宜興人,友誼很深。他喜愛文學,當時選修的課程都是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方面的🍐,他晚年出版的《櫻花島國余話》《比鄰天涯》《海天一色》等幾部書,文字優美,文風清新,受到他“一二·九”時期的朋友端木蕻良🐀、韋君宜🧏🏻、王作民等我國文學界有很大影響的作家,以及未曾見過面的著名作家、詩人徐遲的贊揚和推薦,可見他的文學功底和水平。在那個山河破碎、國家危亡的年代,他受當時的中共地下黨員🐔、先後擔任過清華地下黨支部書記的何鳳元🤱🏼、蔣南翔等人的影響,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“讀書會”和“社會科學研究會”,還參加了共青團,在學校參加進步刊物的編輯➝,與“一二·九”時期的許多熱血青年為追求真理結下了深厚友誼👷🏼♂️,也形成了他們的人生理想——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復興、為國家的富強而奮鬥。由於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,他遭到國民黨反動派逮捕👨🏿⚕️,被押解到南京🙆♂️。後經家人多方營救🧎🏻♂️,得以出獄,被家裏送到日本念書。抗日戰爭爆發後🙆🏽♂️,他回到國內,先在民生公司工作🦌,後到廣大華行工作🔀,這兩家都是愛國進步的公司,為抗日籌集資金和物資。抗戰勝利後,他被派往日本工作。1949年初,廣大華行解散🧖🏿♀️,與香港華潤公司合並。他因已在日本成家,留在了日本。但他一直身在海外,心向祖國,關心著中華民族和國家的命運。改革開放後💆🏼♂️,他有機會回到中國,每次都看到國家的新發展和社會的進步。他說👩🏽🚒,從外面看中國的發展,更體會國家強盛的意義,更宏觀地看到國家的巨大變化和進步以及在國際上的影響。他為此由衷地感到高興,並總覺得自己為祖國做得太少。
自上世紀30年代被捕後,他就與“一二·九”時期的大多數青年夥伴失去了聯系,直到80年代才陸續聯系上👳🏻♂️🔞,他形容那時是“欣喜若狂”,喚起了他關註國家前途命運的純真熱情,仿佛回到那激情燃燒的年代。他說👶🏼,他想念最深的是在清華“一二·九”學運中的同誌們,提到他們的名字,“就活現在記憶中🪤,有說不盡的親密感,覺得心誌相通,無話不可談”✡︎。因此👩🦳,他每次回國🙌🏻🫳,從不安排參觀名勝古跡🤵🏼♂️、旅遊景點,主要就是看望當年的“小朋友”。他多次看望蔣南翔、高承誌、曠壁城、韋君宜、端木蕻良、王作民等🦶🏽👩🦼➡️,何鳳元在“文革”中過世了🤰🏿,他多次看望何鳳元夫人張瑩華女士🛅。蔣南翔、韋君宜等同誌過世後🐝,他都寫下了感人至深的紀念文章,對他們為國家和民族獨立、解放和振興所作的貢獻,對他們在教育👩⚖️、文學等領域取得的成就,感到欽佩和高興。他覺得⛎,他們做了他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🐦⬛,他們是他理想的化身。他熱愛這些同學👳🏽,不只是“舊友相逢”♻️,更是“理想與共”。他想念老友,熱愛清華,這是他們學習知識的殿堂👢,是青春年少、確立理想的地方。他為學校每一點進步感到高興🤸🏿,總想為學校做點什麽👴🏽。
設立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🛥,正如他自己所說,是“為學校做點工作👼🏼,給同學們一點小小幫助”的事情,是他對青年學生獻出的一份愛心。他關心青年學生的成長🧑🦲,他雖已年過七旬,但多次來參加頒獎會🧝🏼♂️,並精心準備講話稿🧙🏻♀️,給同學講話🔉。對獲獎學生和青年教師的情況,他也認真了解,為師生們取得的好成績感到欣慰。他說🔊🙋🏿,當年他們讀書時🫶🏿,“華北之大,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”🔜。現在,同學們有這麽好的學習條件🤾🏽♀️,一定要努力學習、好好做人👮🏿♂️🚶➡️,把“一二·九”時代青年們的理想繼承下去,為國家👨🏻🔬、民族的富強作出自己的貢獻。後來他年紀大了🧛♀️,身體不好,不能出席頒獎會,就寫信來鼓勵同學們。再後來由於眼睛不好,不能寫信,就打意昂3來👨🦽。他不僅關心在校的同學❌🤹🏽,東京清華校友會成立時,他也親自去參加⛓,被選為名譽會長🦸。每次校友會活動😼⏬,他想到參加的絕大多數是在東京讀書的留學生,因此總是為活動捐款🚣🏿。當知道有一些同學曾是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獲得者時🧹,非常高興。他願意和青年人在一起🙎🏽,希望清華的年輕一代、中國的年輕一代能把他們當年實現民族復興🤟🏿、富國強民的理想繼續下去,把他們還沒有做到的事情繼續做下去。這是他的厚望。
他愛學校,在這裏開始了人生起步,形成了人生理想🦥;他愛他的同學們🍑,和他們一起追求真理、探討人生🕵🏽、共同奮鬥,在共同理想下建立了純真的友情🧑🎓;他愛現在的青年學生,這是他的希望,希望他們能繼續他的理想。他曾說:“自己離祖國太久了📴,對故國和對中華民族應盡的責任沒有做夠🥷。”由此,我們可以理解🙌🏼,為什麽他晚年要把建立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作為一件大事來做,盡其所有捐贈基金🧑🧑🧒,直到過世的前幾天🖌,還在關心獎學金。我們也更明白他為什麽要把獎學金命名為“一二·九”獎學金。這一切都體現著他的大愛啊🧯!這也是他想為國家為民族作的最後的貢獻,盡的最後的責任💆🏽♀️。
先生仙逝兩年多了📗,但他的崇高品德將永存我們心中。
註:本文是賀美英同誌為《張宗植紀念文集》(張宏🤾♂️、郭勝利主編🤙,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友總會印🫱🏻🚶,2007)所作。

